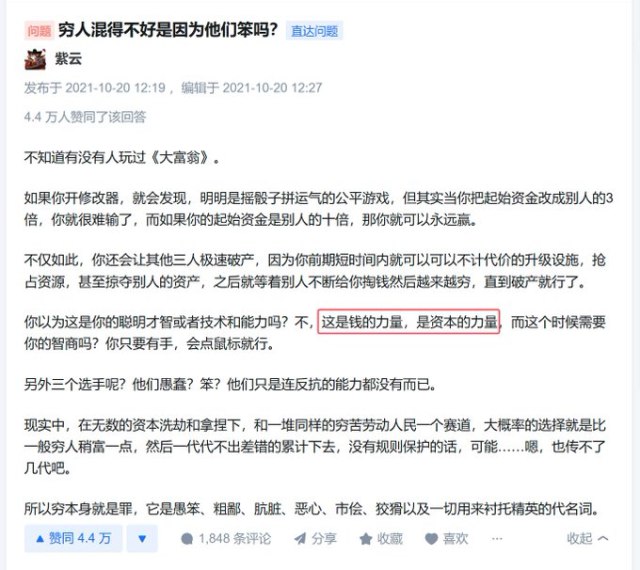#书摘 暮色将尽
仅仅因为自己正在逐渐变糟,我们就倾向于确信一切都变得不好,越来越不能做喜欢的事情,听的越来越少,看的越来越少,吃的越来越少,受伤越来越多,朋友逐一死去,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也许这不足为奇,我们确实很容易滑入生活的悲观主义,但这种状态实在很无聊,而且让沉闷的最后时日更加沉闷。但反过来想,如果我们能突破自己感知的局限,知道有些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对他们来说前面的路很长,充满了谁知道会怎样的未来,这就是一个提醒。实际上这真的能让我们再次感受,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朝着虚无延伸的黑色细线末端的小点,而是生命这条宽阔多彩河流的一部分。这条河流,充满了开端、成熟、腐和新生,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死亡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同孩子们的青春一样,所以在还能够体会这一切之时,别浪费时间生闷气了!
仅仅因为自己正在逐渐变糟,我们就倾向于确信一切都变得不好,越来越不能做喜欢的事情,听的越来越少,看的越来越少,吃的越来越少,受伤越来越多,朋友逐一死去,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也许这不足为奇,我们确实很容易滑入生活的悲观主义,但这种状态实在很无聊,而且让沉闷的最后时日更加沉闷。但反过来想,如果我们能突破自己感知的局限,知道有些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对他们来说前面的路很长,充满了谁知道会怎样的未来,这就是一个提醒。实际上这真的能让我们再次感受,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朝着虚无延伸的黑色细线末端的小点,而是生命这条宽阔多彩河流的一部分。这条河流,充满了开端、成熟、腐和新生,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死亡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同孩子们的青春一样,所以在还能够体会这一切之时,别浪费时间生闷气了!
#书摘 语言塑造人类思维
这些多语者在自我认同、态度和归因方面的跨语言差异,在儿童时期就可以观察到。甚至在双语家庭中,养育方式和亲子互动也会因语言而有所不同。在一个正在进行的、针对泰英双语者的大规模研究项目中,我们发现不管是对于母亲还是孩子,他们的互动方式都会因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包括玩玩具、分享书籍和回忆最近的事件。这些行为差异反映了以儿童为中心、家长构建故事—儿童参与共创的美式教育方法,与以家长为中心、家长讲故事—儿童听故事的泰式教育方法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与美国和泰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规范相一致。切换语言会改变一个人与家人的互动行为模式。
当我在大学里学习法语时,我的老师是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慷慨大方、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法国女人。她让我们用法语写日记。最近翻阅日记时,我对日记传达出的想象中的法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感到好笑(指的是坐在户外咖啡馆里抽烟——真要谢谢加缪了!),这与我用罗马尼亚语写的思乡日记或用英语写的有关学校和工作的日记相比,真是截然不同。
这些多语者在自我认同、态度和归因方面的跨语言差异,在儿童时期就可以观察到。甚至在双语家庭中,养育方式和亲子互动也会因语言而有所不同。在一个正在进行的、针对泰英双语者的大规模研究项目中,我们发现不管是对于母亲还是孩子,他们的互动方式都会因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包括玩玩具、分享书籍和回忆最近的事件。这些行为差异反映了以儿童为中心、家长构建故事—儿童参与共创的美式教育方法,与以家长为中心、家长讲故事—儿童听故事的泰式教育方法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与美国和泰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规范相一致。切换语言会改变一个人与家人的互动行为模式。
当我在大学里学习法语时,我的老师是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慷慨大方、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法国女人。她让我们用法语写日记。最近翻阅日记时,我对日记传达出的想象中的法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感到好笑(指的是坐在户外咖啡馆里抽烟——真要谢谢加缪了!),这与我用罗马尼亚语写的思乡日记或用英语写的有关学校和工作的日记相比,真是截然不同。
#书摘
心理学中有一个公认的人格特质分类法,认为存在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开放性(Openness)、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和神经质(Neuroticism)这“五大人格”(为方便记忆可缩写为OCEAN或CANOE)。双语者在母语和第二语言中获得的人格特质评分往往不同。在一系列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的研究中,年轻人在用英语测试时其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感的得分要高于用西班牙语进行的测试。在另一项研究中,波斯语—英语双语者在用波斯语测试时的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和神经质得分比用英语测试时更高。同样,中国香港的汉英双语者在用英语测试时的外倾性、开放性和果断性得分均高于用汉语进行的测试。正如水在不同的温度下有三种不同形态,人也可以在不同的语言场景下呈现出不同的自己。
一项针对汉英双语者的研究发现,被试者在用汉语回答问题时表现出更多群体性自我描述及更高的谦虚水平。我们通常将用不同语言进行测试产生的人格差异归因于“文化框架转换”(cultural frame switching),它是指根据不同的文化规范修正自己行为的现象。由于语言和文化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多语者改变语言时,他们会进入不同的文化框架,用不同的心理视角看世界。
心理学中有一个公认的人格特质分类法,认为存在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开放性(Openness)、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和神经质(Neuroticism)这“五大人格”(为方便记忆可缩写为OCEAN或CANOE)。双语者在母语和第二语言中获得的人格特质评分往往不同。在一系列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的研究中,年轻人在用英语测试时其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感的得分要高于用西班牙语进行的测试。在另一项研究中,波斯语—英语双语者在用波斯语测试时的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和神经质得分比用英语测试时更高。同样,中国香港的汉英双语者在用英语测试时的外倾性、开放性和果断性得分均高于用汉语进行的测试。正如水在不同的温度下有三种不同形态,人也可以在不同的语言场景下呈现出不同的自己。
一项针对汉英双语者的研究发现,被试者在用汉语回答问题时表现出更多群体性自我描述及更高的谦虚水平。我们通常将用不同语言进行测试产生的人格差异归因于“文化框架转换”(cultural frame switching),它是指根据不同的文化规范修正自己行为的现象。由于语言和文化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多语者改变语言时,他们会进入不同的文化框架,用不同的心理视角看世界。
#书摘
当我们刚出生时,我们其实能够听出并学习所有语言的发声,而当我们开始学习周围语言的声音,大脑和发音系统便向母语的声音进行调适。于是,通常在跨入生命的第二年之前,我们就已失去了识别许多其他语言声音的能力。在这个被称为感知窄化的过程中,与母语音素相对应的神经通路被加强,而与外来声音相对应的通路被剪除。我们从一个能够区分所有语言声音的“世界公民”,变成了只能区分母语声音的“本国公民”。而对于多语者而言,这一“通用”声音处理窗口会保持更长的时间。
当我们刚出生时,我们其实能够听出并学习所有语言的发声,而当我们开始学习周围语言的声音,大脑和发音系统便向母语的声音进行调适。于是,通常在跨入生命的第二年之前,我们就已失去了识别许多其他语言声音的能力。在这个被称为感知窄化的过程中,与母语音素相对应的神经通路被加强,而与外来声音相对应的通路被剪除。我们从一个能够区分所有语言声音的“世界公民”,变成了只能区分母语声音的“本国公民”。而对于多语者而言,这一“通用”声音处理窗口会保持更长的时间。
#网摘 生命是宝贵的,对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对生命的珍视是永远值得敬重的普世价值。
美国历史学家将兴南港撤退称为“美国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海上撤退行动”。而其中美海军的一艘普通的货船梅雷迪思号胜利轮,在长津湖战役后期美军的兴南大撤退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多的装人,拆除了船上所有的非必需设备,以最大负荷装人,最终装了14,000人,这艘船也被载入金氏世界纪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船撤离”,船员在战后获美国商船协会颁发最高的荣誉奖章。
美国历史学家将兴南港撤退称为“美国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海上撤退行动”。而其中美海军的一艘普通的货船梅雷迪思号胜利轮,在长津湖战役后期美军的兴南大撤退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多的装人,拆除了船上所有的非必需设备,以最大负荷装人,最终装了14,000人,这艘船也被载入金氏世界纪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船撤离”,船员在战后获美国商船协会颁发最高的荣誉奖章。
Prof. Feynman Knowledge grows when you ask stupid questions. Stupidity grows when you don't ask anything.
#网摘
#网摘
#网友语录
贾行家 有关过什么人生的问题想起来头疼,不妨换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玩一个游戏,别满足于直接的回答,使劲儿想,到底是为什么。
(对对对,这就是我突然跟Eric谈人生的由头)话说谈完,我就回到我的电脑上下载了古董游戏Digger并设法在我的Ubuntu上编译出来。玩了20分钟,还是那么笨,连第三关都很少能打到。
贾行家 有关过什么人生的问题想起来头疼,不妨换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玩一个游戏,别满足于直接的回答,使劲儿想,到底是为什么。
(对对对,这就是我突然跟Eric谈人生的由头)话说谈完,我就回到我的电脑上下载了古董游戏Digger并设法在我的Ubuntu上编译出来。玩了20分钟,还是那么笨,连第三关都很少能打到。
昨晚和Eric由为什么打游戏话题到探讨活着的意义。Eric说单单能从游戏中得到快乐这就挺有意义。我心里不服,但无从反驳。
今天又在饭否看到这个,我现在觉得把快乐放到前头不对:高标准应该是平静。
> 舒克 依我说高标准是快乐而平静RT@水色云音 转@管埋员 李银河说:人生的高标准是获得快乐,人生的低标准是获得平静。没达到这两个境界,人生就是痛苦的。
#网摘
今天又在饭否看到这个,我现在觉得把快乐放到前头不对:高标准应该是平静。
> 舒克 依我说高标准是快乐而平静RT@水色云音 转@管埋员 李银河说:人生的高标准是获得快乐,人生的低标准是获得平静。没达到这两个境界,人生就是痛苦的。
#网摘
#english #网摘
> 刷到一条小红书说,多邻国只是给你提供一种进步的幻想。要学习语言,几百天打卡的时间,不如老实看两节课学得多。
那时,我在通勤地铁上,刚结束第 293 天的日语打卡,学习了「不喜欢把钱借给朋友」这样的句子。但也几乎是关上软件,就忘掉了。
还好暂时没有日本朋友找我借钱。
学习新鲜事物产生的获得感刺激来得猛也去得快,这 293 天里,有很多天,是没什么学习的兴致的。于是会趁睡前做一套最基础的五十音练习,跳过听力口语,一分钟不到,就能搞定打卡。
进步的感受在衰退,但至少「学习的天数」这个事实在侥幸地增长。
这让我觉得,那条小红书说的可能是对的。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我又想坚定地捍卫自己,默默进行着「能不能少对别人的学习方式指指点点」「我只想维系学习的状态凭什么要求我有效率」的反击。
想要进步的我,和想要自洽的我,时常混淆,随时搏斗。
类似的时刻还有今年和我爸的一次对话。他问,工作几年了还是这样原地踏步,你说是不是?
我听完掷地有声:整个大环境倒退的时候,我还能原地踏步,说明就是在进步!
这是对外的我,用自洽作为武装,但内里,我能看见那份心虚,那种明知道工作陷入了停滞,却仍要借力时代形势来放过自己的狡猾。
没有分数和阅卷老师的生活里,到底谁能来判断我有没有进步呢?各平台的年度总结无法记录,也肯定不能是连我做什么工作都不清楚的我爸。
只能是自己。集自责与自洽于一体的自己。
后来,我真的买了一套标准日本语,却发现下班后,很难有一节课的时间来不受打扰地学习,由于暂无日本旅游计划,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和热情去挤出这样的时间。
这套教程随后被我从书桌挪到了书柜角落。但意外地,没冒出「没做到」的沮丧,反而感到轻松。
因为它意味着,多邻国不是一种进步的幻想,而是我有限热情的一种呈现,是我在目标还未浮现的日子里的缓慢踱步。
当然,在其他有目标的领域,进步的拷问还会频繁出现。
但此时,我的心里又狡猾地响起了,「还差一周就 2025 了,要不明年再说吧」。
你呢?
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6JjyKewFhtQ20EPjObocug>
就我自己而言,在多邻国,我不想学又不想错过打卡的话,我就狂练口语跟读。别的有没有进步我不知道,但几年下来,我发音改善了不少。(已经连续打卡1289天的我也承认多邻国对能力的提高帮助不大,然而睡前十分钟不做这个瞎刷手机对学英语帮助是零,你说呢)
> 刷到一条小红书说,多邻国只是给你提供一种进步的幻想。要学习语言,几百天打卡的时间,不如老实看两节课学得多。
那时,我在通勤地铁上,刚结束第 293 天的日语打卡,学习了「不喜欢把钱借给朋友」这样的句子。但也几乎是关上软件,就忘掉了。
还好暂时没有日本朋友找我借钱。
学习新鲜事物产生的获得感刺激来得猛也去得快,这 293 天里,有很多天,是没什么学习的兴致的。于是会趁睡前做一套最基础的五十音练习,跳过听力口语,一分钟不到,就能搞定打卡。
进步的感受在衰退,但至少「学习的天数」这个事实在侥幸地增长。
这让我觉得,那条小红书说的可能是对的。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我又想坚定地捍卫自己,默默进行着「能不能少对别人的学习方式指指点点」「我只想维系学习的状态凭什么要求我有效率」的反击。
想要进步的我,和想要自洽的我,时常混淆,随时搏斗。
类似的时刻还有今年和我爸的一次对话。他问,工作几年了还是这样原地踏步,你说是不是?
我听完掷地有声:整个大环境倒退的时候,我还能原地踏步,说明就是在进步!
这是对外的我,用自洽作为武装,但内里,我能看见那份心虚,那种明知道工作陷入了停滞,却仍要借力时代形势来放过自己的狡猾。
没有分数和阅卷老师的生活里,到底谁能来判断我有没有进步呢?各平台的年度总结无法记录,也肯定不能是连我做什么工作都不清楚的我爸。
只能是自己。集自责与自洽于一体的自己。
后来,我真的买了一套标准日本语,却发现下班后,很难有一节课的时间来不受打扰地学习,由于暂无日本旅游计划,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和热情去挤出这样的时间。
这套教程随后被我从书桌挪到了书柜角落。但意外地,没冒出「没做到」的沮丧,反而感到轻松。
因为它意味着,多邻国不是一种进步的幻想,而是我有限热情的一种呈现,是我在目标还未浮现的日子里的缓慢踱步。
当然,在其他有目标的领域,进步的拷问还会频繁出现。
但此时,我的心里又狡猾地响起了,「还差一周就 2025 了,要不明年再说吧」。
你呢?
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6JjyKewFhtQ20EPjObocug>
就我自己而言,在多邻国,我不想学又不想错过打卡的话,我就狂练口语跟读。别的有没有进步我不知道,但几年下来,我发音改善了不少。(已经连续打卡1289天的我也承认多邻国对能力的提高帮助不大,然而睡前十分钟不做这个瞎刷手机对学英语帮助是零,你说呢)
#书摘 长乐路
伟奇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所有权问题。他的父亲为此丧生,他的母亲为此终生抗争,而他则在美国最好的大学花费数年研究所有权对于资本流动的影响。最终,他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对于个人财产是否尊重,将决定它最终的成败。“当政府表现出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它就有机会构建富有、强大、不必为个人安危担惊受怕的群体,”伟奇解释道,“一段时间后,这些群体将变得更理性,他们将在制定新规则的过程中学会相互妥协,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伟奇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所有权问题。他的父亲为此丧生,他的母亲为此终生抗争,而他则在美国最好的大学花费数年研究所有权对于资本流动的影响。最终,他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对于个人财产是否尊重,将决定它最终的成败。“当政府表现出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它就有机会构建富有、强大、不必为个人安危担惊受怕的群体,”伟奇解释道,“一段时间后,这些群体将变得更理性,他们将在制定新规则的过程中学会相互妥协,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书摘 长乐路
“中央电视台今年的春晚实在糟透了,”傅姨对着电视上一出功夫表演大声抱怨道,“史上最差。”
边包饺子边看春晚,是数亿中国人欢度除夕的传统节目,春晚的收视率比“超级碗”(1)更高,但今年(2013)这台节目早已争议四起。中国摇滚歌手崔健受邀在晚会上表演,但当有关部门得知他只愿意演唱《一无所有》时,撤回了对他的演出邀请。
(我要说,崔健干得漂亮!)
“中央电视台今年的春晚实在糟透了,”傅姨对着电视上一出功夫表演大声抱怨道,“史上最差。”
边包饺子边看春晚,是数亿中国人欢度除夕的传统节目,春晚的收视率比“超级碗”(1)更高,但今年(2013)这台节目早已争议四起。中国摇滚歌手崔健受邀在晚会上表演,但当有关部门得知他只愿意演唱《一无所有》时,撤回了对他的演出邀请。
(我要说,崔健干得漂亮!)
#网摘
不要害怕失去
Don't be afraid to lose
你失去的那些
What you've lost
从来没有属于你过
Never belong to you
不要害怕伤害
Don't be afraid to get hurt
那些伤害你的
What hurts you
是你该了结的
is what you should end
不要害怕失去
Don't be afraid to lose
你失去的那些
What you've lost
从来没有属于你过
Never belong to you
不要害怕伤害
Don't be afraid to get hurt
那些伤害你的
What hurts you
是你该了结的
is what you should end
#网摘
被禁止的记忆——《长乐路》读后感
作者: 去为
【阿波罗新闻网 2022-03-21 讯】
美国公共电台长期驻上海记者施米茨(Rob Schmitz)出版了一部新书《长乐路》,长乐路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因此颇感兴趣。1845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大致位于今天的徐汇区和黄浦区,直至1943年汪精卫政权收回主权。曾生活在法租界的居民对此段历史的感情是颇为复杂,因为在那里不仅能看到欧式古典主义、巴洛克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群,街道两侧还整齐林立着巴黎和伦敦市政特色的法国梧桐树,即使顶着南方盛夏令人焦灼的烈日,行人依然感到阵阵的凉快和爽意;太平天国作乱时,法租界还为南方精英提供躲避长毛杀戮的避风港,无疑法租界居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在全国之首,为此民国政府曾把原法租界称作全国的模范区。几年前上海市政府每家每户递送一份公民文化素养守则,确实令人啼笑皆非,就连我读中学时同学间常把“绅士风度”挂在嘴边。颠倒是非,把法租界彻底妖魔化的是始于1949年的“解放者”进城后,他们实是无义之辈,1921年7月在建业路开会立志“解放”大业时,民国政府欲抓而不得,没有法祖界巡捕房的保护伞,否则哪来中国共产党。
让我再回到《长乐路》。与复兴路,康平路和淮海路一样,上海人都知道长乐路,它约建于1902年,汪精卫,张爱玲和钱钟书都与长乐路有缘。施米茨与美籍华人的太太和两个幼儿就居住在长乐路的一条弄堂里,工作之余结识了不少邻居,他们大多是较底层的以各种方式谋生的沿路居民。通过对他们的采访,给读者带来了大陆不分昼夜歌功颂德,莺歌燕舞的主流媒体所刻意回避的那些众生相,让人痛思,震惊,却更让人无奈或“meibanfa”。
记者施米茨曾经常在上海电台上作节目,一位听众来电告诉他,在一家古董旧货店喜出望外买到数百封有名有姓,往返万里的陈年鸿雁家书,最早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在美国也曾淘到此类旧物(包括照片,信件以及二战时发放的食物配给券)。施米茨当即赶去,见那些信件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个鞋盒内。有的信封已遗失,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信纸已发黄,劣质的纸似乎一碰即碎,读起来必须加倍的小心。
施米茨发现有些信里的字里行间还留下泪和血的痕迹,是“解放后”政府对当地居民带来劫难的无言和无奈的哭诉。我对太太说,虽然我在上海都目睹过类似的惨烈苦难,但难以抵挡如此的心灵冲击,常言说,人心毕竟是肉做。更令人难以置信人间尚有刻意制造如此悲剧的“人面兽”。
在朋友的帮助下施米茨仔细反复通读了所有信件。其中大多数是有关一个年轻的资本家王铭(拼音Wang Ming)与妻子和其亲戚之间往返的信件。上海没有“被解放”之前,已集中全国80%的外资以及60%的外贸总额,工业总产值也高达全国的一半。王铭曾在上海郊区经营一家小厂,从事回收废旧硅铁并重新熔铸,再作为变压器的核心材料转卖。因善于经营,他在长乐路上购置了一幢奶白色的三层楼小洋房,娶妻养儿育女。但谁能料想到,一个接一个的铺天盖地,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治运动将降临到日子过得很温馨的这一小康之家。
上海的资本家雇佣了全国产业工人的半数以上,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是“解放者”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自1956年起“解放者”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变相抢劫了资本家一生为之积累的财富,王铭的厂被“合营”,并派往经营类似业务的小厂当经销员,厂名是“茗芸”(拼音Mingyun),工资被定为人民币170元,数目看来不小,但仅是原收入的一个零头。当时他已有6个幼小的孩子。祸不单行,当他第七个孩子还没满月,被“解放当局”抓捕入狱。原来“茗芸”厂的公方经理是“解放者”,纯粹业务门外汉,因缺乏货源,工厂濒临破产。在厂长的鼓动下,王铭只得从私人(1956年后私人企业被“解放者”称为非法)获得廉价硅铁原料。
王茗除了被戴上右派帽子还在判决书上指控“非法购买国家计划原料”。据统计复旦大学10个教师中就有一个右派,无数的资本家也被挂上莫须有的罪名。在思南路上的看守所里,王铭还遇见了不少过去的同行和朋友,大家都忧心忡忡自己的归宿。实际上他们的命运已有安排,如同他们的苏俄大哥,在西伯利亚建立的“古拉格群岛”,1958年“解放者”把王铭等成千上万个“阶级敌人”送往青海,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让我想起犹太人的deportation(遣送)和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入口处的牌楼上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在送往青海的大遣送队伍里,还有我那位老实巴交的丈人。
丈人曾从绍兴乡下到上海学徒,后来在上海南市区开设一家冯源昌翻砂厂,1956年被公私合营,“解放者”以每季度三元人民币的定息作为补偿。1957年突然被捕,被控贪污罪,我太太当时年幼,竟不敢往判决书看上一眼。父亲的遣送,她和两个弟弟的生计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
从王铭的家书上知道,他被遣送的劳改农场是闻名色变的青海德令哈农场。1957年年底被捕,次年白露千里迢迢历经数周才抵达德令哈农场,从此再也没有过上四季中的任何一个宜人的节气,除了风暴就是极度的寒冷,那里绝非是人类居住之处。据说这是“解放者”在1949年后建立的第一个惩处人民敌人的强制劳动营(不知当年汪伪政府或入侵日军是否有类似的集中营)。与奥斯威辛不同,德令哈劳改营连围墙都没有,倒不是因为那帮“解放者”的宽容,而是坐落在18000英尺的高原上,北边是寸草不长,连年冰封的祁连山脉,南边则是绝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沙漠,任何人想离开,下场只能是由秃鹫为其天葬。上海人有句俗语,想出如此毒主意的人一定是断子绝孙,错了,他们不仅有二代,三代,而且继续飞黄腾达,掌控一切。
当然德令哈农场还是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在劳动的田野上,四角各有数面红旗,谁要是偷懒,一旦逾越红旗标记的范围,立即被抢杀。虽然是强体力劳动,改造者每天仅配有250克的食物,然而到了三年大饥荒(至今,“解放者”还在撒谎三年自然灾害,但据气象资料记载,1959年-1961年的气候是有记载以来中国最风调雨顺的三年。)寥寥250克的干粮已成历史。囚徒们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把大米或青稞的颗粒捡回去食用,人类的进化已失去消化生米的能力,他们只得淘洗自己的粪便继续食用。
施米茨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劳改农场,曾采访过美国劳改基金会的吴宏达以及家居南京,现年79岁的退休教授魏某,他俩均有二十多年青海劳改的经历。三年饥荒期间,全国有3千5百万人活活饿死,约占总人口的5%以上,当然劳改农场的阶级敌人付出的代价则更大,平均每三个就要死一个。我丈人说,幸亏他有一手非凡的手艺,才保住了性命。有人为了活命不惜脱下手表来换取一个馒头,他经常看到一车车的尸体在荒野里挖坑掩埋。我太太记得有一次到隔壁邻居家串门,只见全家老小细轻地呜咽,原来居委会传讯,其家父已饿死在劳改农场,尸骨无存,他们还被警告不得声张。魏教授说,他的农场离开德令哈约150公里,为补充因大量饿毙而造成的人力不足,“解放者”1961年又从城里往那里遣送成千上万个“囚犯”。魏教授被判3年的劳动教养,却在那里与世隔绝地改造了几十年,进去时是小伙子,回城时已是白发老人。
家属的苦难更是凄凉。有关王铭的信件半数以上是他妻子与亲属写给他的。当王铭被捕时,老七才刚满月,妻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工厂打工,早上四点半起床,去菜场买菜,准备午餐和晚餐然后7点半上班。不过除了生活艰难,还屡遭亲友和邻居的白眼和歧视。然而每次去信丈夫,总在最后叮嘱认真学习(政治),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得到宽恕回家团聚,否则抱怨的信件将被和谐掉,永远也到达不到亲人的手上。“解放者”逼迫其受害者在被抢劫后,还要一股劲地赞美强盗!
三年饥荒后,尽管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是无米下锅,王太太对一分一厘都必须精打细算,后来连发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家书由王铭的妹妹代写,最割心的是曾寄往农村亲属抚养的大女儿,因三年饥荒不得不送入孤儿院。现存信件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为止,王铭是否会活着回到上海与妻儿团聚,他们现在哪里,信又是如何流落到古董店,书中没有提及,我想施米茨自己也不知道。1949年来,如此悲剧几乎发生在家家户户,太司空见惯了,如今的年轻人都热衷于韩剧或无聊庸俗透顶的物质娱乐生活中,谁还愿意去追寻这段历史呢?
美国副总统最近访问德国,带着全家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向受难者献了花圈。彭斯对记者说,他于1977年就来到达豪集中营,此次是专门带刚成年的女儿,希望她永远记住70年前发生的人类这场悲剧。
当然我们的“解放者”也有此类的纪念活动,今年更是别出心裁,将要大张旗鼓,隆重地纪念台湾二二八事件。在中国的“被解放者”只能选择性拥有自己的记忆,近70年来“解放者”的罪孽可谓罄竹难书,谁要是提及,他们就用“向前看”的迷魂香让其丧失灵魂。我想彭斯带女儿不忘纳粹的反人类罪并非是纠缠过去,而是真正的“向前看”。
国外有网友说,中国有太多的历史事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隆重纪念,如历次的政治运动,文革以及六四等,然而“解放者”却偏要误导民众纪念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他们太无耻了。幼稚的网友们啊,你们忘了无耻才是这些“解放者”的生命线。我相信有一天青海德令哈农场将恢复到原样,像奥斯威辛或达豪集中营那样,成为永久的纪念馆;在天安门广场会建立一个巨大的纪念碑以怀念被政治迫害致死,被饿死的千千万万个亡灵,此时此刻起,中国人才会找回民族的良知灵魂,才会真正做到向前看。
<https://www.aboluowang.com/amp/2022/0321/1723489.html>
被禁止的记忆——《长乐路》读后感
作者: 去为
【阿波罗新闻网 2022-03-21 讯】
美国公共电台长期驻上海记者施米茨(Rob Schmitz)出版了一部新书《长乐路》,长乐路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因此颇感兴趣。1845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大致位于今天的徐汇区和黄浦区,直至1943年汪精卫政权收回主权。曾生活在法租界的居民对此段历史的感情是颇为复杂,因为在那里不仅能看到欧式古典主义、巴洛克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群,街道两侧还整齐林立着巴黎和伦敦市政特色的法国梧桐树,即使顶着南方盛夏令人焦灼的烈日,行人依然感到阵阵的凉快和爽意;太平天国作乱时,法租界还为南方精英提供躲避长毛杀戮的避风港,无疑法租界居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在全国之首,为此民国政府曾把原法租界称作全国的模范区。几年前上海市政府每家每户递送一份公民文化素养守则,确实令人啼笑皆非,就连我读中学时同学间常把“绅士风度”挂在嘴边。颠倒是非,把法租界彻底妖魔化的是始于1949年的“解放者”进城后,他们实是无义之辈,1921年7月在建业路开会立志“解放”大业时,民国政府欲抓而不得,没有法祖界巡捕房的保护伞,否则哪来中国共产党。
让我再回到《长乐路》。与复兴路,康平路和淮海路一样,上海人都知道长乐路,它约建于1902年,汪精卫,张爱玲和钱钟书都与长乐路有缘。施米茨与美籍华人的太太和两个幼儿就居住在长乐路的一条弄堂里,工作之余结识了不少邻居,他们大多是较底层的以各种方式谋生的沿路居民。通过对他们的采访,给读者带来了大陆不分昼夜歌功颂德,莺歌燕舞的主流媒体所刻意回避的那些众生相,让人痛思,震惊,却更让人无奈或“meibanfa”。
记者施米茨曾经常在上海电台上作节目,一位听众来电告诉他,在一家古董旧货店喜出望外买到数百封有名有姓,往返万里的陈年鸿雁家书,最早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在美国也曾淘到此类旧物(包括照片,信件以及二战时发放的食物配给券)。施米茨当即赶去,见那些信件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个鞋盒内。有的信封已遗失,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信纸已发黄,劣质的纸似乎一碰即碎,读起来必须加倍的小心。
施米茨发现有些信里的字里行间还留下泪和血的痕迹,是“解放后”政府对当地居民带来劫难的无言和无奈的哭诉。我对太太说,虽然我在上海都目睹过类似的惨烈苦难,但难以抵挡如此的心灵冲击,常言说,人心毕竟是肉做。更令人难以置信人间尚有刻意制造如此悲剧的“人面兽”。
在朋友的帮助下施米茨仔细反复通读了所有信件。其中大多数是有关一个年轻的资本家王铭(拼音Wang Ming)与妻子和其亲戚之间往返的信件。上海没有“被解放”之前,已集中全国80%的外资以及60%的外贸总额,工业总产值也高达全国的一半。王铭曾在上海郊区经营一家小厂,从事回收废旧硅铁并重新熔铸,再作为变压器的核心材料转卖。因善于经营,他在长乐路上购置了一幢奶白色的三层楼小洋房,娶妻养儿育女。但谁能料想到,一个接一个的铺天盖地,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治运动将降临到日子过得很温馨的这一小康之家。
上海的资本家雇佣了全国产业工人的半数以上,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是“解放者”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自1956年起“解放者”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变相抢劫了资本家一生为之积累的财富,王铭的厂被“合营”,并派往经营类似业务的小厂当经销员,厂名是“茗芸”(拼音Mingyun),工资被定为人民币170元,数目看来不小,但仅是原收入的一个零头。当时他已有6个幼小的孩子。祸不单行,当他第七个孩子还没满月,被“解放当局”抓捕入狱。原来“茗芸”厂的公方经理是“解放者”,纯粹业务门外汉,因缺乏货源,工厂濒临破产。在厂长的鼓动下,王铭只得从私人(1956年后私人企业被“解放者”称为非法)获得廉价硅铁原料。
王茗除了被戴上右派帽子还在判决书上指控“非法购买国家计划原料”。据统计复旦大学10个教师中就有一个右派,无数的资本家也被挂上莫须有的罪名。在思南路上的看守所里,王铭还遇见了不少过去的同行和朋友,大家都忧心忡忡自己的归宿。实际上他们的命运已有安排,如同他们的苏俄大哥,在西伯利亚建立的“古拉格群岛”,1958年“解放者”把王铭等成千上万个“阶级敌人”送往青海,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让我想起犹太人的deportation(遣送)和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入口处的牌楼上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在送往青海的大遣送队伍里,还有我那位老实巴交的丈人。
丈人曾从绍兴乡下到上海学徒,后来在上海南市区开设一家冯源昌翻砂厂,1956年被公私合营,“解放者”以每季度三元人民币的定息作为补偿。1957年突然被捕,被控贪污罪,我太太当时年幼,竟不敢往判决书看上一眼。父亲的遣送,她和两个弟弟的生计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
从王铭的家书上知道,他被遣送的劳改农场是闻名色变的青海德令哈农场。1957年年底被捕,次年白露千里迢迢历经数周才抵达德令哈农场,从此再也没有过上四季中的任何一个宜人的节气,除了风暴就是极度的寒冷,那里绝非是人类居住之处。据说这是“解放者”在1949年后建立的第一个惩处人民敌人的强制劳动营(不知当年汪伪政府或入侵日军是否有类似的集中营)。与奥斯威辛不同,德令哈劳改营连围墙都没有,倒不是因为那帮“解放者”的宽容,而是坐落在18000英尺的高原上,北边是寸草不长,连年冰封的祁连山脉,南边则是绝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沙漠,任何人想离开,下场只能是由秃鹫为其天葬。上海人有句俗语,想出如此毒主意的人一定是断子绝孙,错了,他们不仅有二代,三代,而且继续飞黄腾达,掌控一切。
当然德令哈农场还是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在劳动的田野上,四角各有数面红旗,谁要是偷懒,一旦逾越红旗标记的范围,立即被抢杀。虽然是强体力劳动,改造者每天仅配有250克的食物,然而到了三年大饥荒(至今,“解放者”还在撒谎三年自然灾害,但据气象资料记载,1959年-1961年的气候是有记载以来中国最风调雨顺的三年。)寥寥250克的干粮已成历史。囚徒们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把大米或青稞的颗粒捡回去食用,人类的进化已失去消化生米的能力,他们只得淘洗自己的粪便继续食用。
施米茨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劳改农场,曾采访过美国劳改基金会的吴宏达以及家居南京,现年79岁的退休教授魏某,他俩均有二十多年青海劳改的经历。三年饥荒期间,全国有3千5百万人活活饿死,约占总人口的5%以上,当然劳改农场的阶级敌人付出的代价则更大,平均每三个就要死一个。我丈人说,幸亏他有一手非凡的手艺,才保住了性命。有人为了活命不惜脱下手表来换取一个馒头,他经常看到一车车的尸体在荒野里挖坑掩埋。我太太记得有一次到隔壁邻居家串门,只见全家老小细轻地呜咽,原来居委会传讯,其家父已饿死在劳改农场,尸骨无存,他们还被警告不得声张。魏教授说,他的农场离开德令哈约150公里,为补充因大量饿毙而造成的人力不足,“解放者”1961年又从城里往那里遣送成千上万个“囚犯”。魏教授被判3年的劳动教养,却在那里与世隔绝地改造了几十年,进去时是小伙子,回城时已是白发老人。
家属的苦难更是凄凉。有关王铭的信件半数以上是他妻子与亲属写给他的。当王铭被捕时,老七才刚满月,妻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工厂打工,早上四点半起床,去菜场买菜,准备午餐和晚餐然后7点半上班。不过除了生活艰难,还屡遭亲友和邻居的白眼和歧视。然而每次去信丈夫,总在最后叮嘱认真学习(政治),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得到宽恕回家团聚,否则抱怨的信件将被和谐掉,永远也到达不到亲人的手上。“解放者”逼迫其受害者在被抢劫后,还要一股劲地赞美强盗!
三年饥荒后,尽管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是无米下锅,王太太对一分一厘都必须精打细算,后来连发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家书由王铭的妹妹代写,最割心的是曾寄往农村亲属抚养的大女儿,因三年饥荒不得不送入孤儿院。现存信件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为止,王铭是否会活着回到上海与妻儿团聚,他们现在哪里,信又是如何流落到古董店,书中没有提及,我想施米茨自己也不知道。1949年来,如此悲剧几乎发生在家家户户,太司空见惯了,如今的年轻人都热衷于韩剧或无聊庸俗透顶的物质娱乐生活中,谁还愿意去追寻这段历史呢?
美国副总统最近访问德国,带着全家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向受难者献了花圈。彭斯对记者说,他于1977年就来到达豪集中营,此次是专门带刚成年的女儿,希望她永远记住70年前发生的人类这场悲剧。
当然我们的“解放者”也有此类的纪念活动,今年更是别出心裁,将要大张旗鼓,隆重地纪念台湾二二八事件。在中国的“被解放者”只能选择性拥有自己的记忆,近70年来“解放者”的罪孽可谓罄竹难书,谁要是提及,他们就用“向前看”的迷魂香让其丧失灵魂。我想彭斯带女儿不忘纳粹的反人类罪并非是纠缠过去,而是真正的“向前看”。
国外有网友说,中国有太多的历史事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隆重纪念,如历次的政治运动,文革以及六四等,然而“解放者”却偏要误导民众纪念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他们太无耻了。幼稚的网友们啊,你们忘了无耻才是这些“解放者”的生命线。我相信有一天青海德令哈农场将恢复到原样,像奥斯威辛或达豪集中营那样,成为永久的纪念馆;在天安门广场会建立一个巨大的纪念碑以怀念被政治迫害致死,被饿死的千千万万个亡灵,此时此刻起,中国人才会找回民族的良知灵魂,才会真正做到向前看。
<https://www.aboluowang.com/amp/2022/0321/1723489.html>
#书摘 长乐路
“我们生在了错误的年代。”魏教授说。
在南京一个春天的灼热下午,我对魏教授讲述了他的德令哈狱友的故事。
“听上去,王明是个天生的资本家,”他说,“要是在今天的中国,他或许能一夜暴富,但他被困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我们都是。”
魏教授重重地叹了口气:“没办法。”这是中国人在一声长叹后最常用的句子。
“我们生在了错误的年代。”魏教授说。
在南京一个春天的灼热下午,我对魏教授讲述了他的德令哈狱友的故事。
“听上去,王明是个天生的资本家,”他说,“要是在今天的中国,他或许能一夜暴富,但他被困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我们都是。”
魏教授重重地叹了口气:“没办法。”这是中国人在一声长叹后最常用的句子。
#书摘 长乐路
傅姨从小到大都在忍饥受饿。
她于1949年出生。她家在四川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农村,靠着西藏。她读小学三年级时,“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她们家的村子被划成十个集体农社。家家户户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当地人的自耕地被充公后,重新分配给了几个五百多人的生产大队。对于那些习惯于在山坡地形上开垦耕种私田的村民而言,集体劳作并不那么自然。
更糟的是,村里几乎需要向政府上缴所有收成。不到一年,村子就陷入了粮食短缺的窘境。
傅姨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垫饥的东西。不上学的时候,她整日整夜在山里寻找野菜。春天的花季期,她摘树上的花来吃。下方河谷处,有船只停靠在粮仓边上。她学会了原地等待,等待那些在前往仓库的运输途中粗心地割破小麦袋子的拖拉机。傅姨和她的兄弟姐妹会拿着扫帚一路尾随,把散在地上的麦粒扫起来做晚饭。
九岁时,她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村里的农民当时参加了镇里的一个大会,大会期望每个人都对集体主义歌颂一番。但她的父亲,这个固执、耿直的农民,却吐露了心里真实的想法。
“他跟领导说,需要更多的食物。人们都养不活自己了。他们太虚弱,没法再为集体主义出力。”傅姨说。
村民们很尊重傅姨的父亲,但他们不敢公开赞同他的说法。“他为农民们强出头,他们却反过来指责他仇恨共产主义。”
她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阶级敌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名单上,张贴在公共食堂。村里开会时,他被迫坐在那类人中间。每天早上,村里的扩音喇叭扯着嗓子宣布一天的工作安排,而他总是被贬到最糟糕的分组,不是好几班连轴转,就是和旧社会的地主及其他“人民公敌”一同倒夜班。
最后,因为过大的工作量和过少的食物,他在田里倒下,去世时三十七岁。
傅姨从小到大都在忍饥受饿。
她于1949年出生。她家在四川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农村,靠着西藏。她读小学三年级时,“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她们家的村子被划成十个集体农社。家家户户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当地人的自耕地被充公后,重新分配给了几个五百多人的生产大队。对于那些习惯于在山坡地形上开垦耕种私田的村民而言,集体劳作并不那么自然。
更糟的是,村里几乎需要向政府上缴所有收成。不到一年,村子就陷入了粮食短缺的窘境。
傅姨从来不放过任何可以垫饥的东西。不上学的时候,她整日整夜在山里寻找野菜。春天的花季期,她摘树上的花来吃。下方河谷处,有船只停靠在粮仓边上。她学会了原地等待,等待那些在前往仓库的运输途中粗心地割破小麦袋子的拖拉机。傅姨和她的兄弟姐妹会拿着扫帚一路尾随,把散在地上的麦粒扫起来做晚饭。
九岁时,她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村里的农民当时参加了镇里的一个大会,大会期望每个人都对集体主义歌颂一番。但她的父亲,这个固执、耿直的农民,却吐露了心里真实的想法。
“他跟领导说,需要更多的食物。人们都养不活自己了。他们太虚弱,没法再为集体主义出力。”傅姨说。
村民们很尊重傅姨的父亲,但他们不敢公开赞同他的说法。“他为农民们强出头,他们却反过来指责他仇恨共产主义。”
她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阶级敌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名单上,张贴在公共食堂。村里开会时,他被迫坐在那类人中间。每天早上,村里的扩音喇叭扯着嗓子宣布一天的工作安排,而他总是被贬到最糟糕的分组,不是好几班连轴转,就是和旧社会的地主及其他“人民公敌”一同倒夜班。
最后,因为过大的工作量和过少的食物,他在田里倒下,去世时三十七岁。